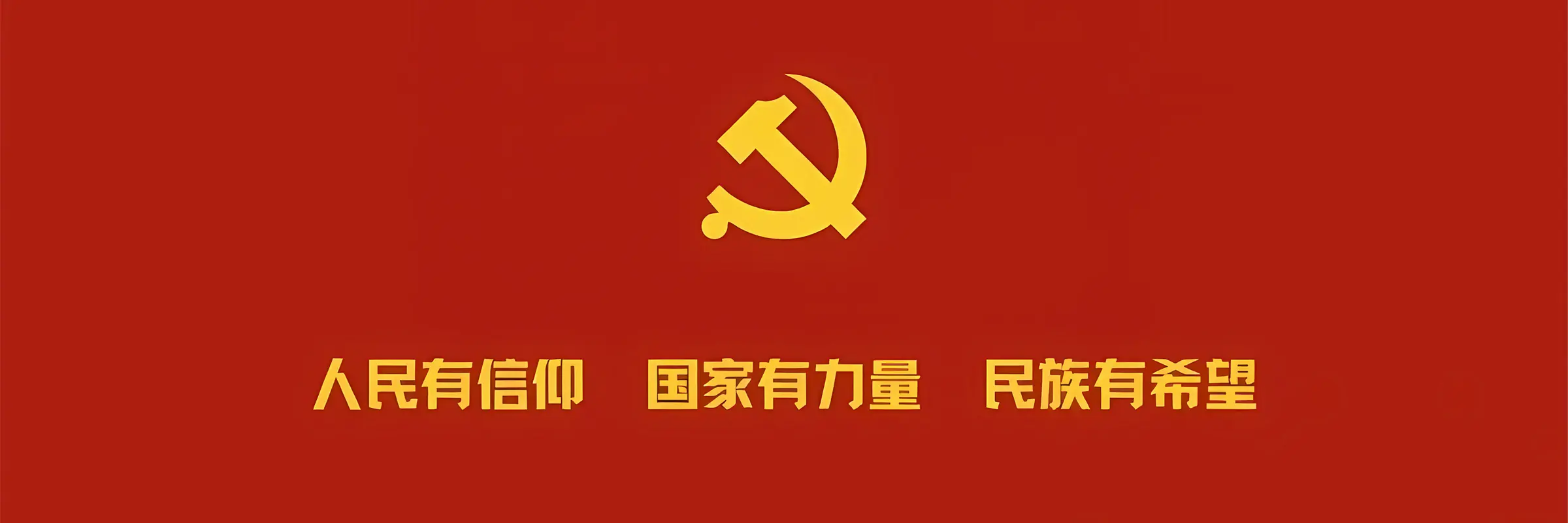序号 UID51
好友55 人
听众3 人
收听0 人
阅读权限100
注册时间2025-2-27
最后登录2025-4-29
在线时间1157 小时
用户组:分区版主
我,秦始皇,打钱
   
UID51
积分6907
回帖555
主题812
发书数335
威望4688
铜币4973
贡献1200
阅读权限100
注册时间2025-2-27
在线时间1157 小时
最后登录2025-4-29
|

对我来说,东北文艺复兴三杰中,班宇的作品最不易读。我偏爱郑执的诙谐深刻,欣赏双雪涛的天马行空。但班宇的小说,既东北又魔幻,似虚无又世俗,天上一脚地下一步,很难长时间沉浸其中。记得两年前一场文学节作家访谈,跻身众多名家新秀的他,诚恳地回答现场提问,反思自己的创作瓶颈,小心透露下一步写作计划。那时忽而升起一种感觉,纵有不少天纵英才光芒万丈,或赢得各大奖项,或获得影视圈青睐,班宇始终秉持匠人精神默默耕耘,探索各种创作方式,或许走得更为长远。至少在这部《缓步》小说集里,看到一个不同以往的班宇。
九篇小说中《于洪》创作得最为精妙。前有日常后有悬疑,架构平衡、情节精彩、语言炼达、节奏轻快,令人生出一镜到底的畅快感。小说融合二十多年前的多个社会热点,抗洪抢险、退伍复员、下岗再就业以及团伙抢劫杀人案。通篇描绘人与人始终无法相互理解的各种形态。爱看书、时常发出一针见血感叹的前妻代表唏嘘人生无意义的一面;暴戾、血腥、阴郁的“三眼儿”和“我”则是人性反覆无常的另一面。人心之复杂,行动之矛盾,在故事中两两相对分外鲜明。“我”对前妻的过去,嘴上接受私下却暴力相待;现任妻子将公司表面托付于“我”,却又无时无刻不在试探怀疑。结尾中“三眼儿”和“我”谁才是参与抢劫杀人的亡命徒,则是一场东北版的罗生门。若“三眼儿”的故事成立,“我”就是一个在抗洪抢险中救下战友一命,却在日后生活中构陷其亡命天涯的大恶人。若“我”的故事成立,“三眼儿”则是一个胆大妄为犯下人命案却在余生中分裂幻想出替罪羊的精神病。小说中所有人都互不信任、彼此伤害却又总试图抱团取暖。也许正如小说结尾“三眼儿”姐弟感叹的那样,人与人之间,没那么亲密,想往一起走,终究还是不太行……剩下的最后这么几步,互相伴着,走完就散,别有负担。
最值得关注的是《漫长的季节》。班宇曾在多个场合聊起自己一直尝试以女性视角进行创作。上一部《逍遥游》出现过一篇,《缓步》里则是这一篇。严格来说,即便将本篇第一人称进行性别转换也毫不违和。即,作者一直希望找到的女性视角在故事中并没有太多性别痕迹。甚至,其对女性心理与形象的刻画较小说集里的另一篇《羽翅》还更为弱化。但与《羽翅》相似的是,故事里都有一个长期瘫痪在床濒临死亡的至亲。前者是女主的母亲,后者为丈夫的父亲。目睹亲人一点点萎靡步入死亡是人生最大的苦痛。无助、绝望以及对人生无常的感叹皆能在此有刻骨铭心的体会。《时时刻刻》里伍尔夫的丈夫问她,为什么要在故事里安排死亡?她说,因为只有死人才能让活人更珍惜生命。但我并不认同故事塑造出的氛围感,即纯粹的温情和留恋。实际,在本篇未直接点明的,却在《羽翅》里借儿媳的口说出:也不知道我们这日子是给谁过的。《漫长的季节》里女主为照料母亲完全失去自己的生活,为完成她的心愿嫁给一个毫无感情且最终离家出走、音信全无的男人。因为母亲觉得“人不畏困境,也不惧斗争,怕的是既没有爱人,也没有对手,睁开眼睛,出门一看,满世界全是疯子和故人,他们中的一部分威胁着你,使你恐惧,另一部分冷眼旁观,因为他们与你再无任何关系。这样一来,过得就很疲惫,没什么想要争取的,也没什么可以期盼的,无事可做,无话可说。” 这些话道理上是一回事,现实中却是另外一回事。长期照料病人,无论是怎样的至亲,也不会是仅有一腔奉献而毫无怨言。而那些卧床不起的亲人也少有书中那般安静,只剩对子女的眷恋。实际上,这漫长的过程往往是一场精神与肉体的双向撕扯。这其中,“渴望解脱” 恐怕才是人类心中隐秘却时常一闪而过的念头。故事里的女性视角,可能还是想象大于现实,母慈女孝的纯粹温情,终究还是活在故事里更多。
与之相对真实的是《羽翅》。一地鸡毛的中年生活,摆脱不掉也解决不了,偶尔的精神或肉体出轨便是最大的脱序与反抗。故事中的三位女性可视作一人,从她们被随意赋予的名字就可看出。刘晓羽、刘婷婷、程晓静不过是千千万万从少女走入婚姻再被赋予母职的女性。她们因婚姻家庭被无端赋予各种本不该承担或独自承担的义务与责任。而始作俑者的丈夫们却可以随时全身而退,甚至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指责批判。父亲可以随时随地晚归甚至不归,而母亲却不敢在孩子身边缺位;丈夫可以因自我感动的孝道将妻子拽入伺候病榻的深渊。即便妻子牺牲自我,也会因几句抱怨而遭全盘否定和责难。《缓步》更像一部中年危机小说集。作者从意气风发地书写下岗潮冲击到心平气和地道出中年的无力。如王小波笔下那只“挨锤”的牛,缓慢、无奈、无论一时如何激愤最终只能回到原地继续挨下去。这也是班宇本部小说集不同以往的主题:人到中年。从首篇《我年轻时的朋友》和第二篇《缓步》便能有所感受。
《我年轻时的朋友》分为四章。首尾两章一如作者既往的写作风格:男女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加之露骨粗俗的吵架式对话。但通篇弥漫着人到中年回望物是人非过往的沧桑与嘲弄。这是经历且仍在经历人生起伏,梦想幻灭、对未来毫无可期的人发出的声声慨叹,有些许悲伤,倒尽是无奈,更多则是心如死灰地继续。未跨入中年门槛的人恐难有体会,正如文中那句“年轻就是好……当时都不以为,过后才能想明白。” 作者不再指天问地探讨虚无与情感,不再竭尽全力展现老工业城的苍凉与哀鸣,而是将它们纳入一段故事的边角,融入时间长河的记忆,标记成人生过客而已。第二篇《缓步》更是将单身父亲独自带娃的经历,化作生活中层层漾起的涟漪,将暗潮汹涌终的过去葬入波澜不惊的当下。日子就是如过不下去般一天一天过下去。亲子关系于人生的奇妙之处便是“再也不需要成为什么,没有愿望,也不想拥有自我”。这篇小说的节奏亦如书名,娓娓道来、缓步前进。
但第三篇《透视法》作者又改变步速,从中年危机鱼跃至意象与现实的交融。这篇故事的人物如无数平行线在无尽的延展中汇集到一个灭点。初中班主任夫妇、女笔友、主人公以及那个预演主人公杀人现场的酒友,都被那只脚上带着黑环的鸽子汇集到了灭点。学生时代的沉闷、下岗潮的苦楚和离异家庭的伤痛,诉说时似波澜不惊,经历时却蚀骨裂心。对过去释怀的人往往是毫无办法的人。又能怎样,能过就过,不能过就分。与生活分手的方式无非如鸽子向高空一跃,只是它们还有翱翔天际的机会,人只有自由落体的命运。向那些被时代裹挟拍脑门子的决定要说法,可谁又稀得理你?作者这段极为精辟的总结“关于逝去的时光,不管是好是坏,人们总要怀着一点虚伪的宽容,并非善待他人,而是开导与劝勉自我,去修饰一个不存在的时刻,如此一来,便没有懊悔,也不会不安,永久立于暴风之眼,成为平静的幸存者。每个人必须相信自己拥有过的那么一点点好运,否则很难继续生活。从这个层面来讲,记忆不是实在的事物,而是虚空之锁,人的精神是钥匙,打开一道又一道,接连不停,过去与未来由此得以汇合。” 这三年来已足有体会。
本集末篇《气象》大概会受到作者书迷青睐。其对应作者上一部小说集《逍遥游》里的《山脉》。同样是集子里的最终篇,同样是将写作者写进作品里。《山脉》里班宇写了班宇,《气象》里班宇写了《山脉》。有趣的情节对照、相互交映、将现实与故事、故事与故事穿插编织成莫乌比斯带,以自我审视的态度书写自我,确是一场奇妙冒险。虚虚实实、神神鬼鬼,正如《气象》中那些上岸的亡魂又被岸边的活人杀死一遍;被妻子否定存在的跳水者,从冰河游上对岸,鬼魅般出现又消失在主人公的世界。《山脉》里的勘探员C,《气象》中有了姓名—陈珂。但正如《山脉》第一章的猜想,一个不存在的人,在《气象》中现身不久又神秘消散于水雾之中。也许班宇下一部小说集的最终篇也会是《山脉》与《气象》宇宙中的一环。这样一种先锋的尝试,新奇的写法,脑洞大开,不知又会导入怎样的意象世界。
2749 个汉字
转自:Violet 评论 《缓步》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489080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