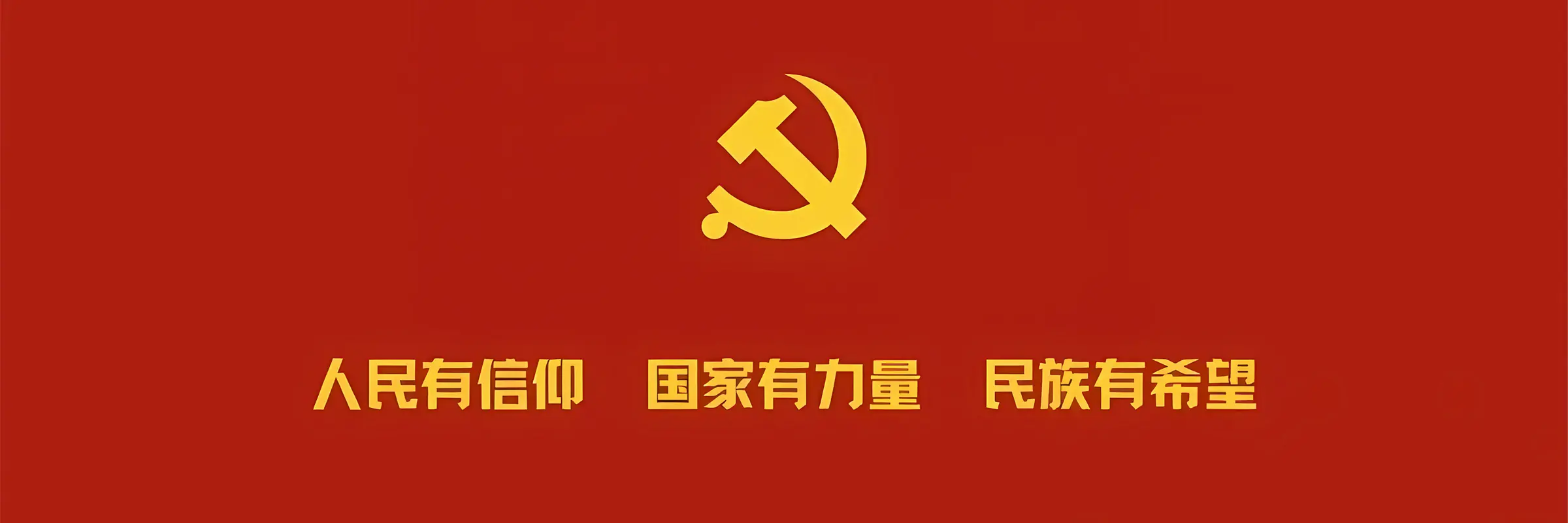序号 UID51
好友55 人
听众3 人
收听0 人
阅读权限100
注册时间2025-2-27
最后登录2025-4-29
在线时间1137 小时
用户组:分区版主
我,秦始皇,打钱
   
UID51
积分6887
回帖551
主题807
发书数333
威望4675
铜币4907
贡献1200
阅读权限100
注册时间2025-2-27
在线时间1137 小时
最后登录2025-4-29
|

如果读者拥有拜读过加缪作品的经验,那么读本书第一行就有强烈的已读感——梅尔索作为默尔索的变体赫然出现,而默尔索作为《局外人》的主角在整个文学史的知名度自不待言;然而其实这部《快乐的死》才是加缪真正意义上的首作,译后记中提到出版的曲折,并称本书为《局外人》的“前传”很是恰当,不仅能再次捋清从Mersault到Meursault的心路发展历程,也可回味加缪如何将自身经历大量投射于此,甚至书中出现的人物皆可在现实中找到原型,因而这部看似体量轻薄的小书,在加缪的作品序列中仍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且译文丝滑通畅,不失为通往加缪世界一个良好的入门机会。
全书共两章,第一部《自然死亡》,第二部《自觉死亡》,读完回温方觉章节标题的字面微妙差异和内里巨大落差。开篇对“四月早晨无情的美丽”之描摹异常动人,繁花似锦,鸟鸣处处,然而早春的喜悦平和场景中马上出现了一个残缺的形象——双腿残肢的札格厄斯,整个第一节两人无对话,通篇是梅尔索的动作描写,在一种几乎是客观冷静的旁观视角中,读者大致掌握到的信息是:札格厄斯是主动放弃生命,而梅尔索则是前来协助完成他心愿的(遗言所及:“我除去的只是个不完整的人。”)
从第一章第二节开始进入的是倒叙,回溯梅尔索与札格厄斯的相识过程,颇为戏剧性的是,札格厄斯是作为梅尔索女友玛尔特的前男友出场的。两人甫一见面,彼此就仿佛产生了某种奇异的认同感,梅尔索一面宣称不喜欢四肢不全的人,一面却乐于成为札格厄斯的听众,后者以缄默的凝重吸引住了这位在阿尔及尔港口厌倦了枯萎光阴的人。那时的梅尔索就已学会叹息着“又过了一个星期天”——生命的倦怠和贫穷的困扰,让他在面对人生的生离死别时,仿佛都已失去滋味;周遭的人还在战争阴影的笼罩中,自戕者和肺结核病人,加缪父亲丧生的那场马恩河战役,现实的图景很大一部分被投射进这部首作中。
札格厄斯为何会吸引住梅尔索呢,就在这之前,梅尔索甚至对任何感情都无动于衷呢,他陪玛尔特玩情侣游戏,欲念目标一旦实体化,就好像能对生活还能产生些许希望似的,他疏懒淡漠的心灵受到一些被奇迹促动的刺激,“差点以为这就是爱情”——并且亲身演绎了一遍情人间乐此不疲的嫉妒游戏,倒是藉由这个机会对札格厄斯有了新的认识。札格厄斯其人,虽抱有残缺之躯,“体内却始终燃烧着对生命光与热的向往”,这种奇异的反差让梅尔索“心底萌生只要再多一分毫无保留的信任,就能称作友谊的情感”,而整本书的余下篇幅都可视作他如何以实际行动去填满这份尚来不及发展就过早夭折的情感。
如果说开篇还无法理解札格厄斯如此毫不惋惜生命的逝去(将生命终局托付给相识尚浅之人),那么在两人交心之后,会约莫知晓他们对生命欢愉和痛苦的认知分歧,以及几乎是浑然天成般达成秘密同盟。他们都曾对生命的辉煌灿烂抱以希冀,梅尔索在穷困的现实中饱尝生命热力的无谓消耗而失去对幸福渴念的信念,札格厄斯在挣得大量资产后依然坚持纯粹的心并为“追求幸福而对抗世界的愚蠢粗暴”。于是札格厄斯希望能帮助梅尔索摆脱金钱的束缚去实现幸福,因为他不仅不允许自己被“残废的吻玷污了人生”,也看清梅尔索同样有一颗纯粹的心。
第二部开始,梅尔索便在欧洲大地上辗转,死亡确信无疑地发生了,无论是终结他人或自己的生命,对个体来说都是颠覆经验的事实。他的五官仿佛被封闭起来,路人老妇人卖的酸黄瓜气味宛如外部世界努力挤进来的一剂猛药,喧嚣的声音和杂乱的气味统统钻进来,“感知突然放大到每一处神经末端”,他终究还是要和世界裂开的缝隙对望。之前,他做过的最大努力是抵御孤独的侵蚀;而现今,他要正视和恐惧的重逢。布拉格红铜色的天空,巴洛克风格的建筑,交织成一种茫然无措的焦灼,梅尔索“变回没有归属、没有去处的异乡人”(注意「异乡人」概念的出现)。他坐火车往北方去,横越过大半个欧洲,将所有力气和念想都停留在飞速后退的风景中,列车与铁轨的狂暴搏斗让他维持警戒状态,动作的迅猛得以保持清醒的认知,从西西里亚平原到布雷斯劳,他终于无法承受满载的沉默,写信给精神之交的女学生们。取道热那亚到阿尔及尔,这是一段清明的回归——充满生生不息的热那亚,混合着沥青和海盐的热那亚,橄榄树指向辽阔天空,女郎的凉鞋踩着温热的石头路面,他意识到即使是最强烈冲动的欲望也仅停留于对肉体深层的渴望,意识到自身的鄙薄和虚假,体认到“纯洁而可怖的爱才是属于他的”。
幸好,他现在因为札格厄斯的遗赠而拥有了物质傍身,因而得以拥有充裕的时间去厘清、界定何谓幸福的存在,他现在有资格砍斫生命本质之外多余的部分,扔掉为生机奔波的杂务,塑造、打磨内核,拥抱纯净、自由的自己,“来直面生命的所有面貌”。阿尔及尔是加缪永远的精神之乡,他最热爱的十个词语——““世界、痛苦、大地、母亲、人类、沙漠、荣誉、苦难、夏日、大海”,一半与之相关。阿尔及利亚夏天的大海给予穷人富人一般无二的珍贵天空,阳光的热力与爱情的芬芳验证生命的自由与伟大,他在这个永恒的内心家园中汲取向内的光明和完满,以追逐光亮的本能寻找超越虚无主义的理由,这些涌动的情感浪潮反复冲刷着加缪,并在后来的作品中无穷复现。
三位女大学生萝丝、克莱尔、卡特琳建立的“世界之窗之家”是一处小小的乌托邦,“就像高挂在灿烂星河中的一叶扁舟”,鲜花植被环绕,天幕下大海和山坡交汇,堪称一个独立于世的隐居点。在此,晨昏变幻,御风而行,思想的刀锋划过平静的表层,思潮的交锋证明此地并不止于清修之所,他们掀起共鸣和震荡的风暴,在星空和烈日下解放自我,体会回归本真的快乐纯粹。他们会探讨女性、子女、爱情、父权制,会追究何谓真正的“快乐——真是绝美的青春,他们尚年轻,掌握着追逐幸福幻影的资格和能力,在秘密心事里享受希望给予的允诺。此处是梅尔索和外部世界的桥梁,或屏障。
梅尔索在“世界之窗之家”短住并获得一些动力后,动身去处理金钱事物以及婚姻问题,未婚妻露西安娜清楚地认识到他并不爱她,然而人们总是这样——被伤透一次又一次,还是会奔赴下次心动;明明看清了婚姻的本质,还会一头扎进去。实在很难想象这是加缪24岁时写成的文字,刚摸到人生一角就已如此“老气横秋”,他不惟看穿爱情(“对自己所爱的人总是一错再错”),更看透了目前为止自己以及世人对“幸福”的定义存有多少偏颇——“幸福意味着抉择”,抉择对于他这样怠惰软弱的人来说几乎是一种不可能,而现在他终于确认了自己逃避的可耻;他也会承认札格厄斯的抉择多么勇敢而清醒。“没有生存的痛苦,就不会热爱生活;伟大的勇气,还在于睁眼看光明和死亡;青春大约就是如此,艰难地面对死亡,有如热爱阳光的动物切身体验的恐怖。”这是加缪在后来作品中写的,原来他很早就这么想了,作为克尔凯郭尔门徒,他从一开始就接受世界的荒谬,真正的勇气是对死亡的漠然,真正的痛苦是空洞的痛苦,我们活着是为了死去,克服对死亡的恐惧才有自由。巅峰期形成的“反抗,自由,多样性”之精粹火花,在本书中已初见端倪,日后默尔索的诞生也在情理之中。
因此,你最终会明白何谓“两人之间完成了一种仪式”,这种仪式,莫如说加缪从写作初期就已奠定思想基础——古希腊式的崇拜美与快乐的仪式,因为对死亡的恐惧反证对生命的眷恋,清醒地意识到死是生存的伟大证明。他的放逐自我演化成对孤独的彻底接受,从此不必再为不被认同而惶惑苦恼,也不再为死亡的突降而惊惧,“人生来面对的就是希望与绝望的混合与交织”。(就像他后来引用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在热爱生活的意义之前,应该首先热爱生活。”)他觉得自己可以理解札格厄斯了,如果没有真正投入和参与自己的人生,那么恐惧死亡则是一种惩罚,如今他借札格厄斯之力,践行了生命的各种可能,达成作为「人」的任务,他把自己交给生命尽头的荒芜,意识无比清明,因为“通往终局的路上一片虚无,没有爱也没有任何矫饰,有点只是属于孤独与幸福的无尽荒漠”,他在死亡面前找到了自由和尊严,这是一种快乐的死。
2858 个汉字
转自:欢乐分裂 评论 《快乐的死》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535329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