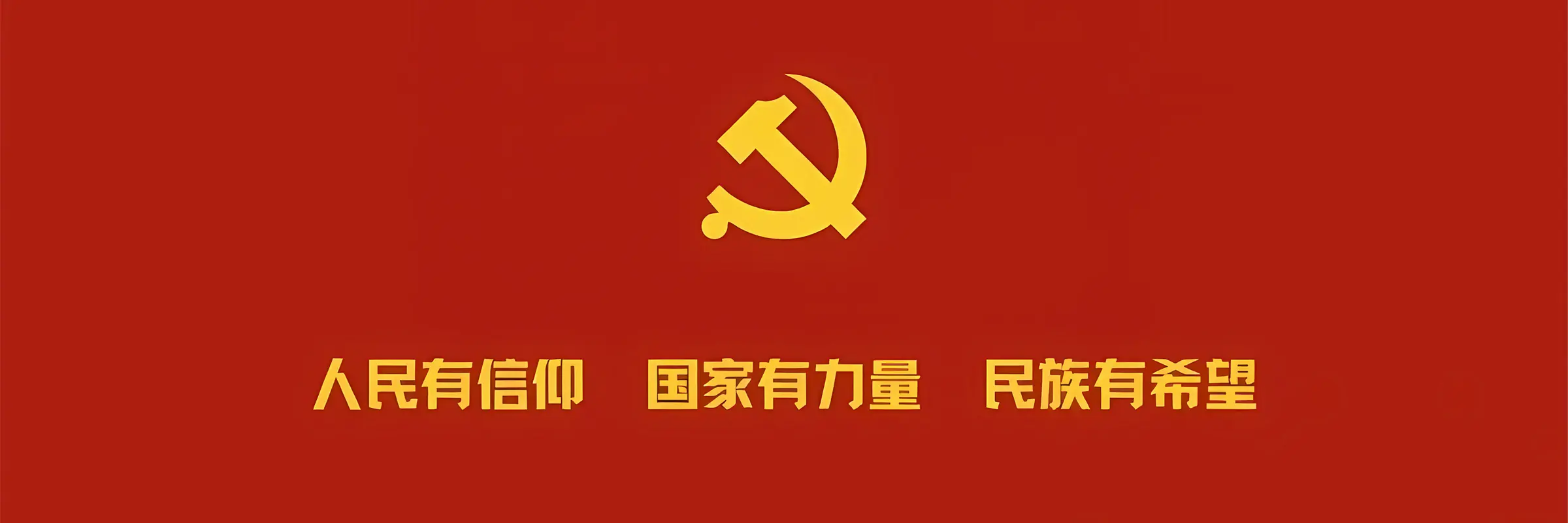序号 UID51
好友55 人
听众3 人
收听0 人
阅读权限100
注册时间2025-2-27
最后登录2025-4-29
在线时间1157 小时
用户组:分区版主
我,秦始皇,打钱
   
UID51
积分6907
回帖555
主题812
发书数335
威望4688
铜币4973
贡献1200
阅读权限100
注册时间2025-2-27
在线时间1157 小时
最后登录2025-4-29
|
徐则臣长篇小说《耶路撒冷》,获得第五届老舍文学奖(长篇小说),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在关于这部作品诸多的评论里,充满了“70后”、“史诗”、“时代”、“成长”、“经验”等等关键词。
小说空间上的首都是花街,北京只是陪都。故事的中心情节非常简单,讲述了几位从小生长在花街的好朋友,因了初平阳要去耶路撒冷读博士后,打算变卖运河边的祖居“大和堂”这件事,一个个从北京向花街聚拢的故事。
作品在结构的选取上做到了恰如其分的创新,形式和内容结合基本完美。情节构图上,以天赐为中心,初平阳、秦福小、杨杰、易长安等主人公围成了互有交叉的外围第一圈,然后以代际为度量向外辐射到父辈和祖辈。
主人公们都暗藏一个共同的心结,那就是儿时伙伴景天赐的死亡——这是作品真正的内在线索。景天赐属于自杀,每个人根本没有任何直接的责任,但是沉重的负疚还是埋藏在主人公们异乡生活的潜意识中,不管他乡的生活是荣耀还是潦倒,澄明还是荒唐。以初平阳卖“大和堂”为契机,这个深埋于心的情结从主人公们心里探出头,伸出芽,泛起波澜,推动了故事向前走。其实耶路撒冷在作品中只是一个符号,一个契合了救赎、信仰、他乡、永恒、回归等主题的符号。异域的耶路撒冷和故乡的花街,形成了作品“到世界去”与“回到故乡”之间的空间张力。
与作者本人和评论家所感不同,也或许是作品真的做到了浑然一体,其结构安排没有给我直接的冲击。让我暗自佩服和惊喜的,是作者的语言。如果不是作者的语言规范、准确、流畅自然,阅读这部长篇巨制将会变成一个灾难。
与典型的乡愁作品完全不同,花街和北京只是一个故事的背景,舞台背后的幕布,重要的是在其中上演的情仇爱恨,悲欢离合。但是,阅读作品的过程中,的确会给读者带来浓浓的乡愁。读着读着,花街,就读成了故乡的名字。
这种精神上的乡愁与古典的莼鲈之思不同。“世界”和“故乡”,两者既是二律背反,又是同义反复。两者不可兼得,两者又互相依存。两者可以指向同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可以是花街、北京、也可以是耶路撒冷,或者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走向世界,也就是走向精神上的故乡,回到故乡,也就是走向精神上的世界。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这部作品的史诗性品格。其实,在作品的主线里,作者把主人公安排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跨度里。那么,评论中所说的“史诗性”何来呢?
关键就在情节构图的外围——祖辈、父辈的故事里。祖辈和父辈有其独立的故事,故事又牵连到初平阳等这70一代人身上,三代人的悲欢交织,因果流转,最后聚焦到的,还是目前的生活,这也让作品有虽不强烈但很明确的现实主义精神。
另一位70后作家李海鹏,在其《晚来寂静》的自序里通过引用一句话表达自己小说的文学抱负,“它试图通过一个人的故事,令古往今来所有人的故事浮现纸面。”徐则臣也有此抱负,《耶路撒冷》这部作品在某种程度上也实现了他这个抱负。
徐则臣自己介绍,这部作品,他酝酿了三年,写了三年,前后用了六年时间。六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说长也长,说短也短。
我想,如果让我把古往今来所有三代人的故事综合一下,大概就是下面这么个说法:
说短,电光火石沧海桑田,白驹过隙一闪而过。年年岁岁花相似,白云苍狗转瞬逝。岁月的人参果还没尝出个所以然,就已被囫囵咽下。
说长,2190个日日夜夜,不能快进,不能跳跃,不能跨越,得一秒一秒的过,一分钟一分钟的经历。四季更迭,依次进行,悠悠岁月像冬天的漫漫长夜,让人无心睡眠。
说不长不短,你知道世界的核依旧坚如磐石。太阳东升西落,月亮阴晴圆缺,周而复始,e=mc2,直角三角形斜边的平方等于2条直角边平方的和……世界的运转像镶嵌在天球上的恒星绕着北极星旋转,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但变化的方式又亘古未变。
但是六年时间在我们眼里,还是换了人间。
当初呱呱坠地的婴儿不经意长成了小小少年,告别幼稚园,正在准备上小学,他已经不再靠着与生俱来的本能生存,开始能诉说,会表达,家庭和社会的影响通过言传身教和大众媒体开始塑造他。信息不断涌入,塑造的过程是个意识层面的布朗运动,充满随机和不定,在不断纠偏和矫正中趋于定型。但此时,时间和未来对他们而言就像宽阔的足球场,依然还有无数种行进的可能。
孩子的父母可能正在经历婚姻中的暗礁,也可能仍然恩爱如初。不管怎样,彼此对彼此的认识肯定会发生一些变化,或好或歹,反正跟六年前本以为的不太一样。但这变化的根源是在比六年前更前的六年,或者再往前的六年,或者继续往前,一直追溯到小小少年,甚至婴儿。总之,最近的六年只提供了阳光空气温度等生长的契机,而种子却早在遥远的某个时刻埋下。
关于个人的疑问需要在个人的历史中寻找答案,一旦把中间的时间隐藏掉,所谓因果,顷刻呈现,命运的脉络于是水落石出,像数学公式推导一般清晰明澈,像剧本一样充满了宿命的安排,像枝繁叶茂的大树底下一定连着根。
只是,推导过程太繁复,繁复到心力只能顾及到眼前的逻辑,让大前提和最后结论暂时失忆,环环相扣中,人的大脑内存只够专注处理逻辑链条里的一环。剧本过程太揪心,揪心到一出折子戏就让我们为人物的命运百转愁肠,忘了再精彩的个人史诗,概括起来,开头和结局无非是一个人出生了,最后他死了。大树也一样,根和树梢之间被旁逸斜出的枝蔓覆盖,让人以为枝蔓就是树本身的呈现,以至于画家笔下的树能开花,却很少能看见树根。
所有前因和后果之间,填满了隔膜,恍惚,漫漶,铺陈,交错。菩萨畏的因和众生畏的果之间,就是梦幻泡影般的旦夕祸福,不测风云,子孙满堂,形影相吊,就是患得患失,手捧流水,就是镜中花水中月,就是无常遍布的大网,你带着你的命运游走其间。
孩子的父母也可能正在经历事业的巨大转型。深耕多年,收入和地位渐渐往上走,通过所谓事业,在社会这个沃土上深深的锲入,和越来越多的人有了越来越多的勾连,存在感十足,初入社会时的螺丝钉幻化为中枢,这让他们产生了世界没有他们将无法运转的错觉。
有运气好的,就有运气相对不好的,以及运气绝对差的。这里头,有的人已经开始缴械投降,有的人还在负隅顽抗,更多人的生命意志是在徘徊,在冲锋或者后退,爆发或者隐忍,进取或者超然,积极或者遁世,刻意或者随性之间。就像面对一场毫无准备的考试,能答的都答了,之所以不交卷,是想看看是否还有意内或意外的机会存在。
少年的父母的父母也许刚熬过一场猝不及防的疾病,或者已经作古。作为已经成为历史的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们已经从舞台上走下,卸了妆,或安享晚年,或被病痛折磨,或儿孙绕膝,或忍受孤独。
如果真有轮回,他们已经顺利卸掉一轮因果,忙着开始下一征程。没有福寿万年,没有万寿无疆,人的极限是百,却总想着万的事儿,到头来,只有挽联上的抬举抵挡着荒诞。如果轮回这事纯粹扯淡,那他们就灰飞烟灭,托体山阿,如露如电,转念成空,至最后,只有亲戚的余悲对抗着虚无。
一切烟消云散,留下的是史诗。
PS:小说第321页,有一句,云淡风轻一轮江月明。就是这句,让我重新看待这本小说。感慨:话,只能入有缘人的耳;字,只能入有缘人的眼。^_^
2490 个汉字
转自:csweiyq 评论 《耶路撒冷》https://book.douban.com/review/8259572/
|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资源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立即注册
×
|